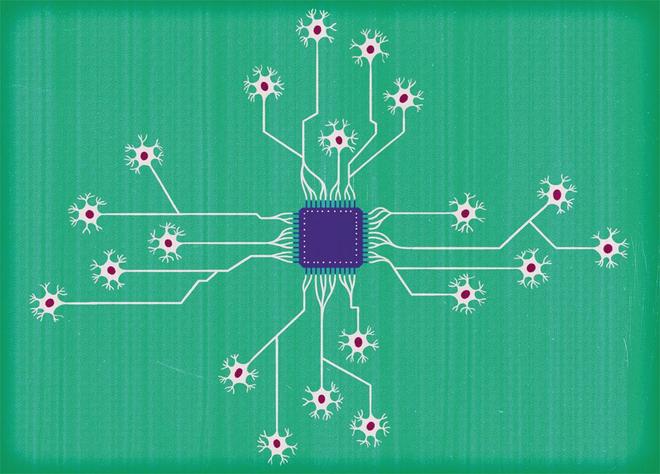欢迎来到“生物计算机”的奇妙世界。在这里,科学家们不再满足于模仿大脑,而是试图直接“驯养”大脑。他们相信,这项被称为“湿件”(wetware)的技术,有朝一日能以一个灯泡的能耗,爆发出超越今天任何一台超级计算机的力量。
梦想的种子:为何要用“活”的大脑做计算?
这一切的起点,源于科学家们对一个完美计算机器的向往:它需要拥有超级计算机般强大的算力,但同时能耗要极低,最好能像我们的大脑一样节能。
我们的大脑,这个重约1.4公斤的器官,运行功率不到20瓦,仅仅相当于一个小台灯的电量。然而,就在这区区20瓦的驱动下,数十亿个神经元每秒钟能完成百亿亿次(10^18)级别的复杂操作。 当今世界最顶尖的超级计算机,比如美国的“前沿”(Frontier),或许能勉强追上这个速度,但它背后是动辄上百万倍的恐怖能耗,足以点亮一个小型城镇!
这种效率上的天壤之别,让计算机科学家们对大脑的构造垂涎欲滴。
于是,两条主要的探索路径出现了。一条是“仿照大脑”,也就是研发“神经形态计算”芯片,试图在硅基材料上模仿神经元连接和工作的方式。而另一条更为大胆的路径,就是“直接使用大脑”——生物计算。既然大脑本身如此完美,何不直接请它“出山”呢?
从零到一:如何“种植”一台生物计算机?
那么,如何“制造”一台生物计算机呢?其过程听起来就像科幻小说。
首先,科学家们需要原材料——细胞。他们通常使用一种叫做“诱导性多能干细胞”(iPS cells)的神奇细胞。这种细胞能被重新编程,变成几乎任何我们想要的细胞类型,包括神经元。
接着,就是“播种”和“养育”。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,为这些干细胞提供合适的营养和生长因子,诱导它们分化成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、少突胶质细胞等各种支持细胞,并让它们聚集生长成微小的3D球状结构,这就是 “脑类器官”(organoids)。
光有“大脑”还不够,还需要与之“对话”。科学家们将类器官放置在一个特制的电极阵列上。这个阵列就像是一个微型“键盘”和“听筒”的结合体:既可以通过电极向细胞团发送特定模式的电脉冲信号,也能监听细胞团产生的电活动。
当电脉冲刺激神经元时,会引起细胞内外离子流动,可能触发一种叫做“动作电位”(action potential)的电信号,这就是神经元在“说话”。电极捕捉到这些“话语”,再通过复杂的算法进行解读,最终转换成我们可以理解的信息。
初试啼声:当脑细胞学会“读”盲文
理论很美妙,但实际表现如何?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机器人研究员本杰明·沃德·切里尔 (Benjamin Ward-Cherrier)和他的团队进行了一次精彩的“概念验证”。
他们的目标是:让脑类器官“识别”盲文字母。
他们设计了一个精妙的实验流程:先让一个装有触觉传感器的机器人去触摸盲文字母,收集数据。然后,将每个字母独特的凹凸图案,转换成独一无二的“电脉冲密码”。
接下来,他们将这些“电码”通过8个电极,传递给一个由大约1万个神经元组成的类器官。类器官接收到信号后,内部的神经元网络会产生响应,电极则负责记录下这片“神经元森林”的活动。
结果令人振奋!研究发现,当输入代表特定字母的电脉冲时,单个类器官平均有61%的概率能稳定地给出相同的响应。如果把三个类器官的“意见”综合起来,准确率更是能提升到83%! 这意味着,这些小小的细胞团确实具备了初步的信息处理能力——它们能区分不同的输入信号。
尽管这还远不及真正的阅读,但这无疑是坚实的第一步。比如,未来或许能让类器官直接指挥机器人行动,形成一个完整的“闭环系统”。尽管基于人脑类器官的闭环系统尚未实现,但2024年的一项研究报告称,一个由小鼠神经元类器官构成的类似系统,已经可以玩名为Cartpole的电脑游戏。
学习的艺术:如何“训练”一团会打游戏的神经元?
要让生物计算机变得有用,关键在于让它们能够“学习”。目前,这些实验室培养的脑细胞反应,更多像是一种条件反射,而非大脑中那种可塑的决策过程。
如何教会它们更复杂的技能呢?科学家们想出了各种办法。
一种思路是使用神经递质,比如多巴胺,作为一种奖励机制。当类器官对某个刺激做出期望的反应时,就给它一点多巴胺,这会强化相关的神经连接,让它下次更倾向于做出同样的反应。
另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Cortical Labs公司,他们在2022年做了一项轰动性的实验:让培养皿中的脑细胞学会了玩经典的电子游戏《Pong》!
他们用的不是类器官,而是平铺在培养皿中的二维神经元网络。研究人员将它们连接到电脑上,屏幕上一侧是神经元控制的虚拟球拍,另一侧是来回弹跳的球。
训练过程充满智慧:
· 如果神经元控制的球拍成功挡回了球,研究人员就会给它们一个“奖励”——一阵有序、规律的电脉冲。
· 如果它们让球漏了过去,就会得到一个“惩罚”——一阵混乱、令人不快的白噪声。
久而久之,神经元网络竟然“学会”了如何移动球拍去击中球,因为它“喜欢”规律的电信号,讨厌嘈杂的噪音。 这背后的原理是,脑细胞天生倾向于重复那些能带来可预测结果的行为。
争议与警醒:“缸中之脑”的伦理边界
然而,随着这项技术逐渐进入公众视野,争议也随之而来。
Cortical Labs的首席科学官布雷特·卡根(Brett Kagan)就曾因在2022年那篇《Pong》论文的标题中使用了“感知力”(sentience)一词而引发轩然大波。约三十位同行联名批评,认为用这样的词语描述一个简单的细胞培养系统是“不合适的,也数据无法支撑”,这种过度炒作可能会让整个领域面临被严格监管甚至禁止的“不必要的风险”。
剑桥大学的发育生物学家玛德琳·兰开斯特(Madeline Lancaster)对此深感担忧。她强调:“一团神经元不是大脑。它不会思考。它不可能思考。” 她担心,如果媒体和公众将这些细胞团与“意识”、“思考”甚至“缸中之-脑”联系起来,可能会引发强烈的伦理反弹,从而导致过于严苛的法规出台,殃及那些利用类器官进行基础脑科学和疾病研究的合规科学家们。
此外,她也对现有实验的实质提出了质疑。她指出,有研究表明,甚至一种完全不含神经元的非生物水凝胶,也能表现出类似“学习”玩《Pong》的行为。 在她看来,在这些简单系统中,我们看到的所谓“学习”,很可能只是一种系统对反馈产生的适应性反应,而非真正的智能计算。
尾声:是星辰大海,还是空中楼阁?
尽管争议重重,挑战巨大,但先驱者们依然满怀热情。从学习玩游戏、到识别文字的初步尝试,生物计算的道路才刚刚开始。
它究竟是通往节能超算的星辰大海,还是最终被证明是难以企及的空中楼阁?答案,或许就藏在科学家们日复一日精心培育的那些微小而充满活力的“细胞宇宙”之中。这场探索,不仅关乎技术,更关乎我们对生命、智能和意识本质的理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