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配图:台剧《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》
家长被焦虑裹挟,按成功模板为孩子规划人生;孩子被繁重的学业填满,失去自主探索的欲望。家长与孩子正集体陷入一种“精神瘫痪”。
双方匆匆忙忙,连滚带爬,活成了两眼空空的“精神植物人”——不思考为何出发,不感知生活本味,只在内卷的洪流中机械前行。隐秘的精神休眠,正蚕食着生命的活力,成为现代人最沉默的困境。
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项飙教授在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副主编吴琪的对话中,抛出的一个观点,他说:
“当代年轻人正陷入‘精神植物人’状态,对现实无感、逃避社交、沉迷虚拟世界、丧失生命热情。”
他认为,当一个人的大脑被持续性、高密度地占据时,他就会陷入一种机械性思维状态——不再主动思考“为什么要做”,只被动执行“应该怎么做”,这本质上就是精神层面的瘫痪。
可怕的是,在这个时代,精神瘫痪的“植物人”比比皆是,却不自知。

最新直播预告 港校申请越来越像一场玄学。有人成绩亮眼却被拒,有人平平被录取。申请港校,不是输在成绩,而是输在信息滞后和节奏错乱。 不同港校之间的有什么定位差异?同一所学校不同专业的真实录取难度又是如何? 本周三晚上7点半,听唯寻「老法师」Jack老师讲述如何抢先将十几枚港校录取收入囊中?深度解析在当下的港校申请的竞争局面中,普娃精准破局。


港校申请越来越像一场玄学。有人成绩亮眼却被拒,有人平平被录取。申请港校,不是输在成绩,而是输在信息滞后和节奏错乱。
不同港校之间的有什么定位差异?同一所学校不同专业的真实录取难度又是如何?
本周三晚上7点半,听唯寻「老法师」Jack老师讲述如何抢先将十几枚港校录取收入囊中?深度解析在当下的港校申请的竞争局面中,普娃精准破局。
“精神植物人”
项飙教授指出:“精神植物人”的诞生,不是个体养育的失败,而是系统性压力下的集体异化。
《要有光》一书中有这样一位“别人家的孩子”雅雅。她从小在妈妈的严格要求下,在内卷的赛道上一绝红尘,领先众人,自我要求极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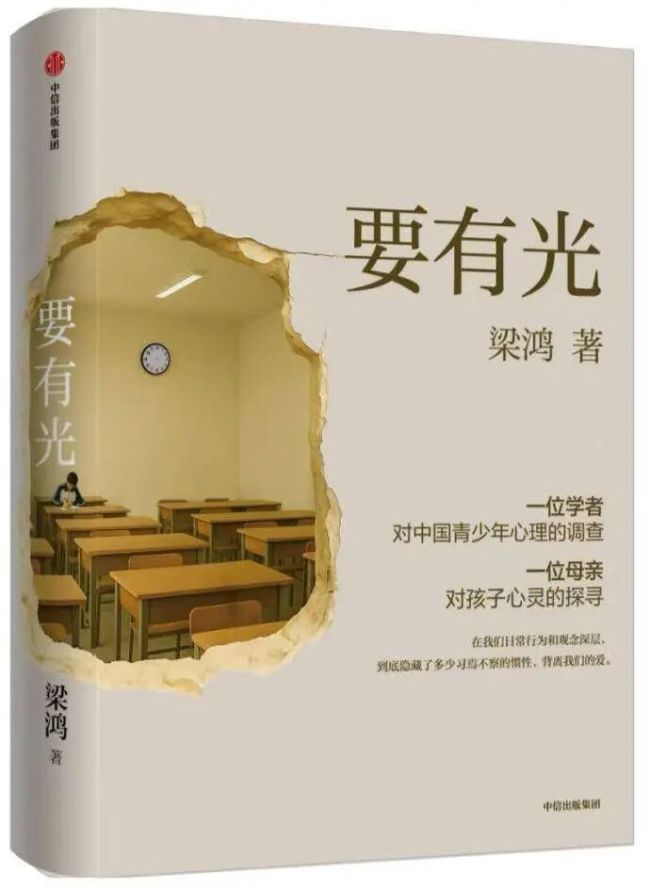
可是,在升入滨海顶尖高中后,牛娃如云,这让难以再稳拿第一的雅雅精神愈发紧张,与日俱增的焦虑让她甚至无法参加考试。一次语文小考,同桌写字声在她听来像倒计时,满脑子“他要超过我”,虽认识每个字却读不懂句意。到最后严重到无法进入教室,只能休学。
2021年5月家人带她就医时,她突然精神崩溃,而妈妈比她更崩溃,一声声哀怨地暴哭,犹如尖刀,加剧她的病情。
后来,因服药产生严重反应,雅雅终日昏昏欲睡,妈妈带朋友家访时,她不堪聊天的“噪音”持刀乱舞(实为想自残),妈妈竟然叫来精神病院救护车,把她绑进精神病院。
但为了“看着”她,妈妈又谎称自己也有病,要求共同住进病房。

住院期间,她被迫“表演正常”,见院长、医生就说“我好了”,最终才得以出院。那段日子孤独无助,她形容自己就像演《肖申克的救赎》,每天都在伪装,生怕自己“不正常”就被永远留在那里。
在整个挣扎、自救、疗愈过程中,妈妈给的是密不透风般窒息的爱,爸爸则是用下跪的方式“胁迫”她——“你赶紧好起来上学去吧,你不好我们就活不下去了”。
如果说“不敢停下”的学习压力是外部的巨石,来自双亲矛盾的爱,则是刺痛她的利刃。
尽管出院后的日子照样过,可情绪就像被按了暂停键——笑不出来,哭也没力气。这种说不清的疲惫,像慢性缺氧,慢慢吸走了活着的力气。
就像在过“精神植物人”的生活,明明活着,却像行尸走肉。
整个社会都病了,
大家却仍趋之若鹜
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%,50%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。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,社会亟须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。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-20%,接近于成人。有研究认为,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病。
生病的孩子,往往有个生病的家,77%和69%的学生患者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易出现抑郁。63%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苛/控制、忽视/缺乏关爱和冲突/家暴。
这是《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》给出的数据。
梁鸿教授在书中哀叹——
“整个社会都在编织出一套东西来,考试机制、民间教育机构、各种升学教育的竞赛班,还有各种利益集团,给家长制造出一个狭窄的通道,让大家自相残杀。”
最终,整个社会都病了,集体挂着氧,眼神空洞,精神无望,却还在硬撑着向所谓的“成功”匍匐前行。

在奥数班中连轴转到晕倒的男孩,醒来感慨:“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,但停下就会被淘汰。”当整个评价体系变成单一赛道,所有人都成了赛马场上的赌徒,眼里只有终点线,忘了为什么出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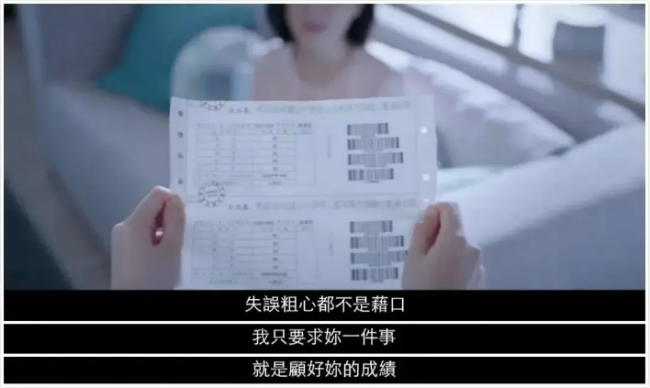
中国人民大学的梁鸿教授在写作《要有光》的走访中遇到了“全职陪读妈妈”陈清画,她就是典型代表。
为了让儿子吴用全身心学习,陈清画的付出近乎偏执:从两岁起便规划好教育路线,双语幼儿园、各类培优班从未间断,初三更是一门心思押注数学竞赛,坚信这是通往清北的捷径。
她放下身段求人,砸重金请名师,把吴用送进北大名师的竞赛班。为节省通勤时间,她每月花一万八的月租租住了学区附近的老破小,只为让儿子多睡半小时。她的手机里全是“升学交流群”、“补课资源群”,每天盯着群里的消息,生怕错过任何“关键信息”。
“别辜负妈妈”是她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,也是让吴用惧怕的紧箍咒。

吴用本是个对数学满怀热忱的天才,初中便自学微积分,痴迷于数字背后的逻辑之美。但妈妈陈清画以“为你好”为名的极致付出与严密管制,最终将这份天赋与热爱碾碎。
“她虽然口头上支持吴用,认为竞赛过于功利,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,但实际上,她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、刷题,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,她几乎是威逼利诱......她利用了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,并在最后无情地说,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。”梁鸿教授在书中戳穿了这份以爱之名的绑架。
当吴用在集训营凌晨两点睡不着打电话哭诉时,妈妈却只让他“再坚持两天”便匆匆挂线。可是长期的精神压迫还是让他无法坚持,失眠、头疼接踵而至,他开始了歇斯底里地争吵,哭喊着控诉这种只有学习的生活如同行尸走肉,让他“一想到考试就窒息”。
最终,陈清画不得不退出家长群、停掉竞赛班,接受儿子休学的现实。可她心里慌,在无数个他闭门不出的日夜,只能不断踱步于门前,默念着“快点好,别落后”。
正是这种“不卷就焦虑,卷了更焦虑”的恶性循环,让每个参与者都如陈清画般,身不由己。
望子成龙的父母倾尽所有,失去了自己的人生;压力山大的孩子负重前行,根本没机会拥有“自己”的人生。为了所谓的成功,丢了自我,机械而迷茫。
在这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中,两代人都在无形的漩涡中病入膏肓。

父母的爱其实都有鄙视链
“在我们日常行为和观念深层,到底隐藏了多少习焉不察的惯性,背离我们的爱?”
中国人民大学梁鸿教授在《要有光》中抛出的这句灵魂叩问,揭开了内卷时代最矛盾的做法:我们拼命为孩子铺路,却亲手折断了他们感知世界的触角;我们焦虑于“不能输在起跑线”,却忘了教育的本质是让人成为“人”。
忘了初心的父母被焦虑裹挟,又用焦虑压迫孩子,最终谁都没有活出“成功”的模样。

《要有光》里开办心理咨询业务并设立特殊补习班的阿叔,在见过太多被“爱”压垮的孩子后,痛斥部分父母严重缺乏对孩子的共情能力。
“他们一味迷信学校的权威、医院的诊断,还有那些成功学的陈词滥调,唯独不肯相信自己的孩子,也不愿静下心来倾听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。”
在补习班任教十几年的丰丽
老师,谈及自己多年从业与家长打交道的过程中,深刻体会到一种残酷现实——“当你的孩子成为差生的时候,你发现父母的爱是有限的。”

因为在家长看来,成为“差生”就等同于人生彻底失败,而这样的失败,家长是难以接受的。
翻看《要有光》中的那些案例,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现象:但凡对孩子前途尚存牵挂的家长,都会将孩子厌学、弃学的表现,直接等同于自身教育的失败。
那个小考失利后在房间里划伤自己的16岁女孩,母亲怒斥“我都做到这样了,你还想怎样”,女孩抬起鲜血直流的手臂,心里的痛却远超身体的痛——“我不是不努力,我只是实在太累了。你们只看见分数,根本没有看见我。”
多少家长也是如此,听懂了成绩,却没听懂孩子。于是,孩子放弃了倾诉,选择了沉默。
梁鸿教授在书里描述了孩子们是如何一步步“撤退”:从学校退回家中,从客厅退回房间,从现实生活退到手机屏幕里。
“再退我没得可退了,我只能自杀。”
所以,我们会看到这一代的孩子,有的沉迷网络,逃避现实;有的揭竿而起,叛逆造作;有的抑郁消沉,休学在家,有的无力反抗,干脆选择一跃而下……
还有更多的人是“精神瘫痪”,活成了“有呼吸、有行动,却无灵魂”的精神植物人。

要有光,
才能看见光
“我突然意识到,我无法回应和触碰我孩子的痛苦,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,而是因为,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。在以爱为名的种种行为和话语中,我,我们这些自诩为爱孩子的人,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。”
所幸,及时醒悟的家长,大有人在。
梁鸿教授在《要有光》中记录了一个令人欣慰的转变案例:
月月情绪低落、持续腹痛时,妈妈第一时间捕捉到异常。当女儿说“大脑控制不住想不开心的事”,她立刻放下工作,带女儿从内科查到心理科,即便初期无器质性问题,也始终坚信女儿的痛苦真实存在。
确诊后,家人达成共识“孩子的健康最重要”。妈妈全程陪同月月做心理干预、复诊,咨询后不追问细节,只默默递上热牛奶静静陪伴。爸爸学习青少年抑郁知识,避开“要坚强”等无效安慰,转而用拼图、动漫等互动帮助她减压,在她失眠时静坐床边守到她入睡。
月月同意返校前,妈妈提前和老师沟通,恳请减少作业、不强调成绩,送校时,轻声承诺“不舒服就打电话,我马上来接”。返校后,家人从不主动问学习,只聊“饭菜合不合口”“有没有开心事”。
尽管曾被确诊中度抑郁伴精神病性症状,但正是家人的最坚实的接纳与守护,如细水长流的光,温柔托住了陷入阴霾的月月,让她重新站起身,看到希望。

“当我们愿意在‘一米之内’做出微小改变时,光就这样慢慢漏进来了。”
慢慢的,奇迹发生了!月月的情绪逐渐稳定,脸上重新有了笑容,更意外的是,她的成绩不仅没有下降,反而稳步提升。
在日记里,她写道“以前刷题的时候,我总觉得脑子像生了锈,越急越学不进去。现在练完书法再做题,脑子突然变灵活了。我发现自己不是讨厌学习,是讨厌被强迫着学习。我想考个好高中,不是为了让爸妈满意,是为了以后能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。”
当我们还在追问如何成功时,月月用自身的“重生”告诉我们:“生命力的生长需要空间,当孩子有机会接触真实的世界、追随内心的热爱时,内在的学习动力自然会被激发。”

很多时候,孩子的“精神休眠”,是被父母的焦虑传染的。
我们把所有期待都压在孩子身上,把自己的人生暂停键按下,美其名曰“为了孩子”。可一个连自己都不快乐、都迷茫无助的父母,怎么能养出阳光的孩子?
只有让孩子先看得见光,他们才可能成为光。只有给孩子足够的尊重和空间,灵魂才有机会苏醒,生命才有机会生长。

父母“爱的留白”,本质上是“放下焦虑”的双向救赎。
当父母愿意卸下紧箍咒般的焦虑,松掉事无巨细的控制欲,践行减法教育,减少课外班、减少比较、减少焦虑,开始寻求从从容容,游刃有余的真实人生。
让子们重新找到童年肆意奔跑的快乐、收获同伴嬉笑打闹在的笑声;让人间真实的烟火气重新回到生活,社会拂去浮躁功利的喧嚣;那些“休眠”的精神气,那些被压抑的生命力,都会慢慢醒来,我们才能见证“精神植物人”的复苏。